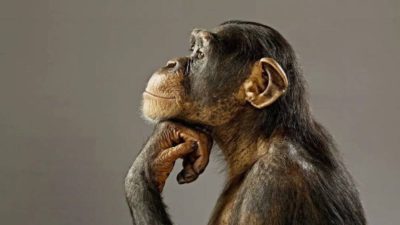在日常生活里,我们鲜少做出或说出令自己惊讶之事,因为我们习惯了脑海中的声音,任由其左右。我们时常沉浸在自我审视中,倾听内心声音,依据它来界定自身观点,还会笃定地说“那不是我会说或做的事” 。
我们把这种内心熟悉感,大脑自行编造的“剧本”,当作自己的身份。一旦想法与身份划上等号,谈论想法就等同于谈论自己。
如此一来,想法和身份认同之间便产生了张力。文化与经济都以理念为根基,随着时间流逝,社会上许多想法不断优化,可仍有部分固步自封。这些陈旧或有害的想法,被一些人视作自身身份的一部分,只有当秉持这些想法的一代人退场,它们才会逐渐消退。
这使得建设性对话变得艰难。人们有时虽渴望改变部分想法,却难以割舍与之相连的个人意志。因为一旦失去这些想法,仿佛就失去了部分身份,所以我们很少主动寻求改变自己的身份 。